
原标题:徐城北走了,他曾从老北京写到新北京|逝者
10月11日上午7时30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徐城北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徐城北的女儿徐佳于当日发布了讣告。讣告中还表示,因疫情防控要求,一切后事从简。

讣告截图。
徐城北生前专注于对京剧艺术和京城文化的研究,著有《老北京:帝都遗韵》《老北京:巷陌民风》《老北京:变奏前门》《梅兰芳与二十世纪》《京剧与中国文化》等各类著作。

徐城北,笔名塞外、品戏斋,1942年生于重庆,在北京长大,1965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历任中国京剧院编剧、研究部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京剧一百题》《梅兰芳与二十世纪》《京剧架子与中国文化》《老北京:帝都遗韵》《老北京:巷陌民风》《老北京:变奏前门》等。(照片由郭延冰于2006年摄)
在2006年,新京报曾专访徐城北先生,请他口述个人的生活、思考和写作经历。当时他六十多岁,不断回忆过去,在口述中感叹,“现在这些前贤很多人都走了,我自己也步入了老年。那些回忆都成了我后半生的宝贵财富”。
以下为徐城北先生口述旧文《徐城北:做新时期的旧文人》。重发以纪念。
口述丨徐城北
早年经历:离开北京,回到北京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妈妈在《大公报》做过记者,笔名子冈。家里的文化背景,给我带来非常深厚的影响,像沈从文先生、聂绀弩先生、常任侠先生等一大批老先生,都是妈妈的朋友,这些老人对我都非常钟爱,都愿意把自己那一肚子学问教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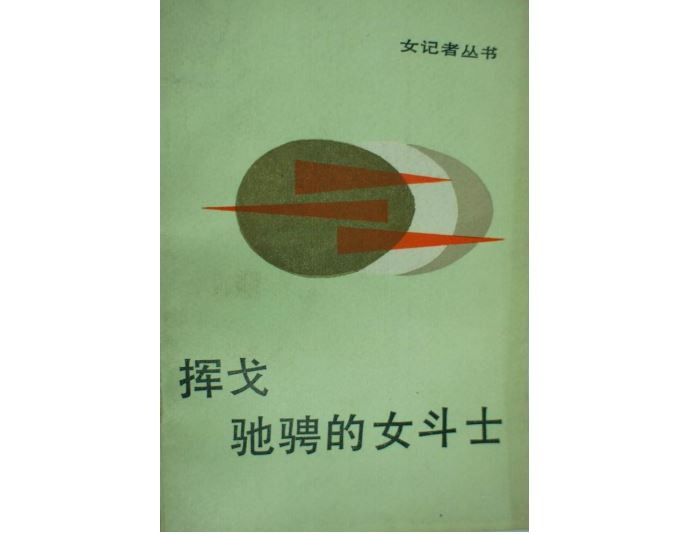
《挥戈驰骋的女斗士:女记者子冈和她的作品》,徐城北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3月。
当时有个青年作家浩然,他忠告我说:“城北,你缺少的不是笔墨,你应有自己的第一手生活,这样你写东西就会源源不断了,谁也抢不去了。当然,我也不主张你去普通的农村,那样跟你的气质和专业也不契合。你需要特殊的生活基地,只要你能一竿子插下去,三五年必有所成,生活不会埋没人的。”我觉得很对,没过多久,妈妈在我们家那台十二英寸的小电视上看到了反映新疆建设兵团的报道,看了之后妈妈问我:“你愿不愿意去新疆?”
我想了想说,去!
1965年,我就到了新疆,在新疆一待就是八年。到新疆若干年之后我才猛然发现,我家庭周围的那批老人身上的和身后的文化,是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我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又不是说割断就能割断的。我开始思念沈从文、聂绀弩、吴祖光那一批老先生,甚至比思念我的父母还要强烈。我开始希望离北京近一点,离他们近一点。
一度北京市的河北梆子剧团要我当编剧,但户口解决不了。河北梆子剧团把解决我户口的问题报到了市委,市领导答复说:北京有很多文艺干部下放在农村,有什么理由从新疆调一个青年的文艺干部呢?后来我又想去唐山,也没去成。

《中国京剧》,徐城北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年10月。
最后我选择了河北省固安县,我直接找到县委书记,自报家门,说明我的家庭跟自己都是什么情况。我说得很坦率:“我想到这里来,但是不准备在这里干一辈子的,将来你一定要放我回北京。”那个县委书记说:“完全理解,不过你来了要先卖把子力气,好好干几年,将来我一定把你送回去。”没想到一干又是七年。
后来回北京,我还真不是靠“后门儿”,凭的完全是自己。我曾把一个写回忆新疆生活的剧本寄给了中国京剧院,最初无非是想征求一些意见,没想到他们看了之后,直接就给我发了调令。
进京剧院十年三写梅兰芳
很快我就被调回了北京。
回了北京之后我开始就是一门心思想搞编剧。我有生活和文字上的积累;我有几位难得的好师傅———京剧圈里有范钧宏﹑翁偶虹,文化界有吴祖光和汪曾祺。干了不到三年,文化部长在春节讲话中说到京剧团要搞承包,剧团要打破原先的建制,重新组成小分队为不同的观众群服务。这样一来,演员们也不排新戏了,把创作人员甩在一边,忙着赚钱去了。当时剧院领导安慰我们说:“等暂时的混乱过去之后,工作还会有的。”我在台下补了一句:“面包也会有的。”我心想,我的师傅们可以等,唯独我不能等,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成就已经奠定了,唯独我还是一张白纸,如果若干年后我还是一张白纸,这个地方我就不能待了。
我进入京剧院时,笔头比较活,新诗、旧诗、散文、杂文写过不少,当时我父母的那帮老朋友纷纷复出,担任了诸多报刊的主编,我投稿不愁发表。正好京剧院也不用坐班,我就撒笔写开了。写了半年一年之后,吴祖光和汪曾祺都托人带话给我:“城北啊,你写得太杂了。这些东西是你在新疆的、在河北的生活,而不是你在京剧院的生活,不是你作为一个编剧应该写的生活。京剧院现在虽然乱,但终究是块宝地,袁世海、李和曾都是国宝级的演员。不要看京剧演员说话不利落,认字有限,但京剧文化是直接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只不过是没有人把这些内容勾连在一起,你正应该担当起这种勾连的工作。”我听了这种规劝,就开始把自己的研究创作集中在梅兰芳身上了。

《这里是老北京》,徐城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当时梅兰芳已经去世多年,我为什么选择梅兰芳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呢?因为我在京剧院接触到那些健在的老先生,许多大牌演员在回忆自己时总难免带着吹嘘成分,我就是想找一个比他们还大气的人压住他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梅兰芳最合适,梅先生虽然走了,但去世的时候岁数不是很大,而且他是中国京剧院的第一任院长。我母亲采访过梅兰芳,她周围的一些朋友跟梅先生也熟识,在这样的基础上,我调集了大量的资料,又采访了梅兰芳的家人、弟子包括尚、程、荀这三个家庭里的人。
这样的工作让我对于梅兰芳及其同辈成长的年代文化背景有了细致了解。
这样,我就开始写书了,1990年我就出版了《梅兰芳与二十世纪》,后来一不做二不休,咬定青山不放松;1995年,我又出版了《梅兰芳百年祭》;到了2000年,我又写了一本《梅兰芳与21世纪》。这就是朋友们所说的“十年三写梅兰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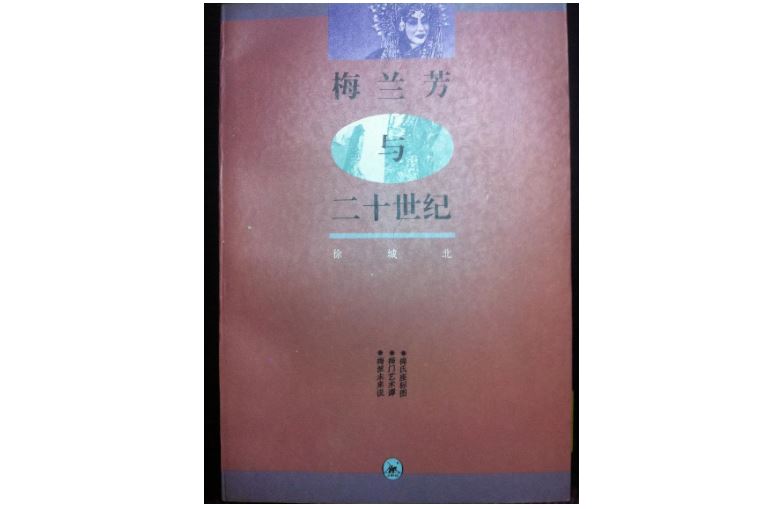
《梅兰芳与二十世纪》,徐城北著,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版。
从老北京写到新北京
实际上,到了1995年前后,京剧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京剧大势已去,要说进步是在文化层面,在理论上,唱腔上进步不大。就是在那一年,我开始寻找我自己新的研究方向。正好当时江苏出版社来北京组稿,找人写老北京的稿子。我说:“我正在写《京剧和中国文化》,还差个尾巴。”但是他们咬住了我,非让我写。
我想自己有研究老京剧的底子,对于老北京的事儿也比较熟,就应承下来。写完《京剧和中国文化》,我就开始写《老北京》,在那本书中,我凭着对老北京感性的直观认识,写了一些老北京的旧事,出版之后卖得非常好。于是我跟出版社说:“一本我还没有写过瘾,我想变换角度逐渐深入,写一个三部曲。”出版社让我拉了一个提纲,他们看了之后就同意了,我次年就出了《老北京2》,随后又写了《老北京3》。
写完了《老北京》三部曲,我58岁了,离退休还有两年,出版社的朋友跟我说:“城北兄,你60岁就得退休了。我们有个建议,既然你写了《老北京》三部曲,如果你的身体和脑子还行,在2008年之前再写出《新北京》三部曲如何?”我觉得这建议可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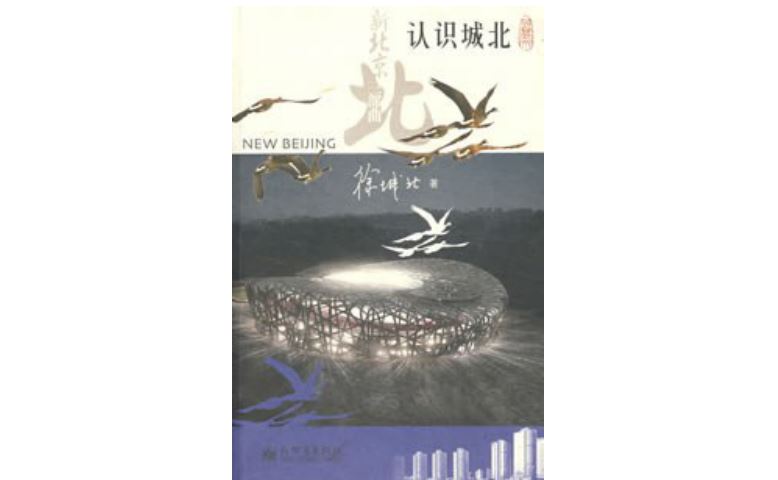
《认识城北》,徐城北著,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6月。
就这样,我从北京城南搬家到现在这个地方———新北京的城北,徐城北这下子真的住到了城北!
搬到这里我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在我《新北京》的三部曲中,第一本就定名为《认识城北》,这个城北不是我本人,而是新北京的城北。
现在这本书已经写完了,第二本也已经写了一半,在这本书中我回到城南,描写新北京的城南,第三本我计划写新北京的左东右西,东到通州,西到门头沟,而且在东西之中,还牵扯到“中”———既包含北京城的中心区,也把中国哲学上的“中”的内容也融会进来。
沈从文送古董
这些内容都写完之后,我打算掉头往回转,极力做一名“新时期的旧文人”,回到沈从文、汪曾祺、聂绀弩那一辈老人的传统中去。说到我和那些老人的精神联系,可写与可琢磨的东西太多。
比如说我对沈从文的认识,是从我自小在沈从文的膝盖下玩的时候得来的。我33岁结婚的时候,我们家在平安里,沈从文那时住东单,他坐着111路无轨电车到了我们家,送了一点小礼物,一个是五蝠捧寿的清朝盘子,上面贴的红字是他自己剪的。还有一个,在一张小小的红色洒金纸上写了他对我与妻子的祝福:“祝两位多福长寿———为国家多做好事为多福,长寿则可以为国家多做几十年好事。从文敬贺。”别小看这纸小,那是故宫里的古纸,非常名贵。

《京腔话京剧》,徐城北著,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1月。
至于汪曾祺,他算是叔叔辈了,但是我始终叫他“先生”。后来我跟汪先生比较熟悉的时候,我也成人了。中国作协组织作家采风团,我们俩都是成员,他是年纪最大的,我是年纪最小的。同时我俩还都是大连日报文艺部的顾问,有一年夏天,大连日报组织笔会,我和他都去了,住在棒棰岛。晚上吃完饭之后,很多当地人就拉着汪先生写字画画,汪先生觉得自己一个人去未免孤单,就拉着我和苏叔阳一块去。我去了,写了几幅字就不写了,站在汪先生旁边看他画,一遇到出色的就“截留”了下来。
现在这些前贤很多人都走了,我自己也步入了老年。
与健在的老人见面的机会虽然还有,但像以前那么在一起玩的机会,却很少很少了。
那些回忆都成了我后半生的宝贵财富,不要说写进文章了,就是想上一想,心头也充满了幸福感。
逝者新闻作者|何安安
旧文口述丨徐城北
旧文采写丨陈远
关于我们 合作推广 联系电话: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电子邮箱:zht@china.org.cn
版权所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京ICP证 040089号-1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10120170004号 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