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湘西到广西,作家田耳的生活越加规律,教书、看书、写作,田耳说以前自己从前还有想着玩,现在就想多干活,每天多写一点。内在节奏越加稳定,岁月往昔里的那个江湖就不停地冒了出来。年轻跑生意时听来的一句“我可以叫孔雀开屏”和一位有点异能神不楞登的朋友重合了起来,让骄傲的孔雀应声开屏,这样的奇巧淫技,现实中未必有,小说中不妨在,于是就有了《开屏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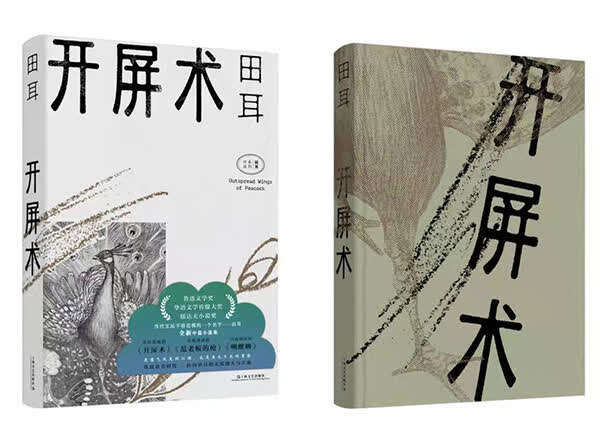
《开屏术》
近日,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70后青年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田耳的全新中篇小说集《开屏术》,包含《开屏术》《嗍螺蛳》《范老板的枪》三部中篇小说。田耳曾经凭借《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鲁迅文学奖得主。近年来他始终笔耕不辍,接连刊载了不少兼具文学性和故事性的优秀作品。上海文艺出版社将田耳的过往作品结集成册,形成了田耳作品系列陆续推出,《开屏术》为其中第四本。2020年已经推出了《天体悬浮》《衣钵》《环线车》三本。
《开屏术》中生意人易老板为了讨好一局长,想送其一只能听从人指令可随时开屏的孔雀,于是引出几年前第一次养斗鸡便出其不意战胜易老板的“酒鬼”隆介:易老板对他怀着一种莫名的隐秘的信赖,这桩“养孔雀”的买卖就交给他来做,由此一项异想天开的献媚计划徐徐展开,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田耳笔下,易老师、隆介、凌大花共同演绎了一部肆意凌厉又荒诞伤感的江湖传说。
《开屏术》的生动精彩不仅打动了读者,也摘得了2019年《收获》文学排行榜中篇小说榜榜首。《收获》对其评价为:“《开屏术》以工匠精神缓慢稳实地铺展想象空间,基于写实间杂夸张因而略显荒诞,讥时讽世但主体平和宽厚,在揭示时代荒诞的同时又透露出人世的温暖。”借新书出版之机,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田耳,走进他笔下的丛林江湖。
田耳记忆中八九十年代才有的江湖气息现在已经消失,“那时小县城里打架狠的是名人,最狠的才找得到漂亮女友。我小时体弱多病,只能当看客,经常目睹打架斗殴,一边看一边随时准备撒腿跑开,怕被误伤。一晃两千年以后,全民赚钱,当年打架狠的大哥多是在路边摆烧烤,以往的名气仍可稍稍招徕生意,兑现零钞。我坐下撸串,看着挥汗如雨的大哥们,心头多少闪烁着荒诞感。那时的朋友多是反差极大的性格交织于一身,卑微与狂傲,狡黠与憨厚,呆滞与躁动,多情与压抑,痴情与放纵……那时候,我们都还在活在像个人的路上,青春漫长,内心挣扎,怀有理想,也时常滑入无边的寂灭和绝望。”
时代变换,将人与人之间纠缠不清下的尴尬和窘迫,轻轻地熨烫平整。田耳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羡慕,看着如今洁净、体面,甚至不乏优雅,取着彼此雷同的港式台式姓名的小孩,仿佛胎教就已完成了“活得像个人”的训练。田耳觉得,人还是应该有那么一段不体面。
田耳笔下的隆介,看似神不楞登,人堆里不声不响甚至还有那么点猥琐,偏就身怀某种异能;他若夹起尾巴做人也能稳赚钞票,偏就喜欢将日渐美好的生活折腾得七零八落仿佛与周遭人事,与生活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隔膜。但不管日子折腾成何等模样,仍禁不住他脸上的欢悦,内心的狂喜,仿佛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是一种全新体验,值得期盼。他强健有力的心脏泵出的却是王八血,品味他这个人,鸡汤和毒药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你困苦时从那找安慰,你得意时从那找平静。
这样的隆介在人群中不是独一个,在田耳看来,中国前20年蓬勃的发展离不开这种折腾起来叫外人看来自不量力的“隆介”们,那些叫人咋舌的事情,回头去看,不可思议又似乎顺理成章。

【对谈】
澎湃新闻:你在《开屏术》的创作谈中提到了自己曾经的江湖岁月,聚集了很多文艺创作者的“青年之家”,对过去的回忆怎么和训孔雀这么一个奇思妙想联合在了一起?
田耳:二十年前,我在湖南最小的一个县级市生活。穷困潦倒说不定是文青的标配,但大家都满不在乎。写作之初,曾经混迹在当地文艺界一位好事者自创的“青年之家”。《开屏术》里的主角,原型就是偶尔来“青年之家”客串的朋友,写字作画,也在地方报纸上发小块文章。他偶尔出现,活灵活现,和我们不同的是,他既能搞艺术,更擅长赚钱。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似乎一直葆有某种古怪的激情,别人在变,他体内某种天真一直持续,跟我吹嘘艳遇与财运,或者新近又认识哪一位地方要员。
我很喜欢这个朋友的画,很有点天分,但日常生活中的猥琐也是不可忽略的,这两者非常奇妙地融合在一起。我工作后跟的老板,他做过餐饮,也卖过孔雀,所以我对孔雀有那么一点了解。这两个人物单独写,一直写不好,而我忽然有一次想到把这两个人合在一起,结果就产生了化学反应。

澎湃新闻:隆介训练孔雀开屏,这种对不可能性的开掘和想象是否代表了一种对待庸常的日常生活的反抗?在他身上你是否寄予了某种人性的理想?
田耳:我可能不太在意意义层面上的东西,意义是好故事里自带的。这个故事的源头,是我年轻时候跟着老板去谈生意,有个人说了一句“要是可以发个指令让孔雀开屏,它就开屏,那就值钱了”,孔雀是不可能听人指令开屏的,这个人是怎么想的?我就记在心里头了。
我一直觉得,中国前20年的奇迹发展包涵了每个人的自不量力,老外看不懂,其实我们自己也看不懂。人们常说中国人保守,但你看民间发生的事又充满着想象力,每个人都在折腾自己干不了的事。如今再回头看,那些叫人难以想象的事,竟然好多都成了。
澎湃新闻:书中易老板和“我”其实都不太把训孔雀当回事,他们能够容忍隆介诡异的行事风格,是因为把这个人这件事作为生活在别处的一种补充和寄托吗?
田耳:生活里都得有那么个补充,有点能力的人更容易对把握不住的人充满敬意。所以民间骗子多,有的是真骗,有的是半真半假,有的不觉得自己是骗子,最后也做成事了。这就是郁达夫的那首《钓台题壁》中所说“不是尊前爱惜身, 佯狂难免假成真”。
澎湃新闻:隆介始终把“存在的可能性”视为他的人生目标来对待,无论是训孔雀,还是追求更令人把握不住的凌大花,他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还是一个江湖英雄?
田耳:两者都有,这个人物原型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他心有不甘,他想进体制,亲近领导,又看不起领导,而领导也不傻,自然把他的轻视看在眼里。我看过渡边淳一的回忆录《何处是归程》,在他20多岁时,一群写作的朋友聚会,其中一个朋友作家说自己看淡了,以后不要任何奖项。渡边淳一他们就很感慨,因为他们那个圈子可能说出这句“不要”,就代表着言出必行吧。但我们身处的环境,谁都说过不在乎功名,但谁真的不要呢?谁又会相信呢?所以我说我们的环境难以自证清白。
澎湃新闻:有评论说你的小说有着感怀青春、致敬江湖的意味,你理解中的江湖是什么?
田耳:我现在临时给“江湖”定个义,因为人和人关系亲密,从而产生彼此约束的感觉,其中的人以此为乐。谁都不能完全认同谁,谁又离不开谁,一百块开一桌夜宵,几斤散酒,可以把小城的艺术家或文艺青年聚足十来个,漂泊感十足。如今生活好了,你找个豪华地方吃宵夜,一是邀不到人,二是宵夜最需要人与人相濡以沫的感觉,一豪华这就感觉没有了。现在人与人没必要那么亲近了,江湖自然就消失了。所以我既不是致敬,也不是讽刺,我只是还原。不过我个人还是喜欢现在这种淡,我特别宅,喜欢一个人待着。
澎湃新闻:你说过回忆过往发现,幸福的高光时刻从未扎根在脑海,倒是当初的不体面和尴尬窘迫一直很鲜活。
田耳:我会感慨时代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赋予人的气质是不一样的,我当初进入社会做生意时,那就是一个丛林社会,没有人不被骗。坐个绿皮车我感觉每一回都受到人格的侮辱,因为秩序的失衡人们挤作一团,互相叫骂。但人和人之间因为种种碰撞,因为种种尴尬,彼此之间就形成不可言说的紧密关系。现在高铁精确到秒,位置分明,秩序的失衡就消失了。人和人之间很淡,是因为优雅了。以往的关系是不可言说的,现在是点赞之交,微信把人的关系变得赤裸裸,过于直接,又有点无聊。
澎湃新闻:隆介身上有着复杂的张力,天真又市侩,身怀异能才气又有点猥琐,鸡汤和毒药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将虚假的优雅碰碎一地,这是隆介的魅力吧?
田耳:生活语境中的虚假和懦弱一直在伤害我们的生活。年龄越大,越有说真话的冲动,要不然心中的无意义感会与日俱增。但在生活环境中,是很难的。我曾遇到过一个朋友,他说自己从不说假话,我当面就说,不是怀疑你的人品,而是你的语言技术达不到,你的语文得有多好,才能从不说假话又不和身边的一切相抵触?在我们的语境里面,偶尔冒出一点真话,别人就觉得很真实。别人说我很真实,我真实什么呢,人怎么可能独自真实。少说话,多写,在小说里通过虚构接近真实,那是很爽快的。书里一个老作家评价隆介是个演员,“我”憋不住张口一问“谁又不是演员呢?”
所以我写小说,就不想为难自己,也不想为难读者,说白了,你总得让人看得下去。你让人家看不完,丢人。别说啥风格流派,你没写好,才总结什么风格流派,你写好了要让读者喜欢看,欲罢不能地看。我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明白,得有娱乐精神。我自己的阅读需求就这样简单直接:在欲罢不能之余,作者还能塞给我意想不到的道理,让我觉得某种高级,那我佩服他,感谢他。《开屏术》受欢迎,我也有些意外。

田耳作品系列
澎湃新闻:这本书中第二篇小说《嗍螺蛳》是“舌尖上的中国”的味道。
田耳:写《嗍螺蛳》我的目的很明确,我要写出80年代的气味,一种老小说的味道。20年前,你只要请客,请8个人,最后能来10来个人,那是年轻时的饥饿感,火锅吃完了大家还没过瘾,继续买两颗大白菜还能再涮一涮。现在请客都很难,吃饭都成为一种负担,所以我们才发现,其实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饥饿感。我看到有人的一句评语,特别精准,“《舌尖上的中国》,就是让别人替我们吃”。所以在这篇小说里,我想通过文字找寻下那种饥饿感。
澎湃新闻:《开屏术》《嗍螺蛳》都有一种和日子肉搏的拼劲,使劲折腾。但《范老板的枪》气势急转而下,是看似成功之人的日暮。
田耳:对,《范老板的枪》是反江湖的。这个灵感来源于早年间做生意,遇到过一个老板,他对我的朋友说“能不能帮我做掉一个人”。这个老板没什么文化,他可能是用词不规范,不清楚“做掉”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代人的青春荷尔蒙是港片制造的,也许这个词是看香港警匪片学来的。
范老板想要雇人做掉自己的司机蔡老二,然而他发现,当他想把财富兑换成强权时,对方反而抓住了他的软肋,轻易凌驾在他之上了。我想表达的是,每个人各有其位,你的安稳和话语权只在你安于那个位置的时候,而妄想会将你推到弱势的位置上,离开你的身份你啥都不是。最后范老板颓然发现拿不回话语权了,那就自我安慰下,通过一个假装射杀蔡老二的游戏,找回自己的面子,而司机还是那个司机。这就是犯位后要归位。
澎湃新闻: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位置感”?
田耳: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意识。小时候看武侠片,很多人喜欢代入,因为故事里的英雄快意恩仇,有花不完的钱,有无数爱自己的美女。可我就想,那你要是故事里的小人物呢?照样贫困潦倒,可能开头就死于乱战。警匪片里也是这样,枪的出现明明是消除体力差别的,一个老太太也能用枪杀死一个壮汉,但影视剧里的子弹还是长眼睛,而且是势力眼,永远懂得级别,先打中小弟,再逐级杀掉大佬,这个逻辑我觉得很好笑。
写作要想得到别人认同,必须保持清醒。有的书很容易被抛弃,因为认知有问题,这是很严酷的事实。在年轻脑子还好用时,就要给自己判定几条标准保持清醒。对我来说,小说一直写下去,如果读者抛弃我了,我就收手,给自己留一点尊严。很多时候,被读者抛弃就因为写不好,但我们总是要找许多莫名其妙的理由自我安慰。
澎湃新闻:据说你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这次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田耳:新故事里,我又还原了江湖,我挺有武侠情结的。80年代武侠小说进入大陆,基本都是盗版,印刷质量非常低劣,我们把这种书叫“黑书”。我收藏“黑书”的过程中享受到了一段历史故事,那个时候的台湾,有很多当兵的人在写武侠小说,有个军情局的特务也在闲暇时写武侠,我就从这切入了。小说已经写好了,正在修改,看看能不能早日发出来吧。
关于我们 合作推广 联系电话: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电子邮箱:zht@china.org.cn
版权所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京ICP证 040089号-1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10120170004号 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0105123